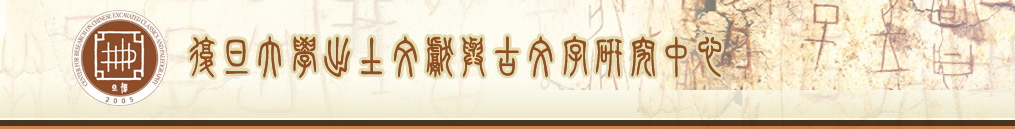
2016—2023年敦煌马圈湾汉简研究综述
(首发)
王玉婷1 韩树伟2
(1.甘肃简牍博物馆 甘肃兰州 730030;2.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敦煌马圈湾汉简自发掘出土以来,在同时期全国各地简牍陆续出土、公布的影响下,加之简牍自身条件和保存环境的限制,释读研究工作呈现出进展慢、质量不高的特点。近十年来,《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通过红外扫描高清图版取得新的突破并使得简牍再整理成为可能,随之推动各方面的相关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发展趋向。文章重点对2016—2023年敦煌马圈湾汉简相关研究情况作一回顾和梳理,希冀裨益于学界。
关键词:敦煌;马圈湾;汉简;研究综述
引 言
马圈湾遗址是汉代敦煌郡负责西北方向防御的玉门都尉下辖二候官之一玉门候官所在地。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县文化馆在河西对汉长城进行联合调查中,意外发现了斯坦因遗漏的马圈湾烽隧遗址(编号D21),并发掘出土简牍1217枚,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研究汉代与西域交往乃至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①]
早期的马圈湾汉简,在1991年由中华书局以《敦煌汉简》[②]出版。随着红外照相和印刷技术的成熟和运用,2013年张德芳主编的《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③](以下简称“《集释》”)出版后,马圈湾汉简再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白军鹏博士学位论文《敦煌汉简整理与研究》[④]及论文修订后出版的《敦煌汉简校释》[⑤],在综合已有学者释读的基础上,对包括马圈湾汉简在内的全部敦煌汉简进行了详细梳理。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⑥]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整理马圈湾汉简释读、释文及说明有关问题的著作,参考价值较高,对马圈湾汉简再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此,笔者着重对2016—2023年敦煌马圈湾汉简相关研究作一回顾和梳理,旨在为学界同仁提供学术上的便利。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释文辨识校正
简文释读的准确性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近年来,马圈湾汉简释文辨识考证工作持续“求真出新”,简牍文字初始整理之后,需经过多次推敲修订,才能逐渐臻于完备,达至善本。
(一)未释字探论
张丽萍、王丹《<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未释疑难字考》[⑦]藉助图版,讨论了旧有释读的缺漏字,文章综合利用草书、碑刻、敦煌文献等材料,选取《集释》字形清晰完整但释读难度大、未能隶定的五例未释字进行讨论,对有误之处给出释文并加以说明。
(二)误释字订正
张丽萍、张显成《<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释读订误》[⑧]在核对图版的基础上,征引《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额济纳汉简》等简帛材料,发现《集释》十则误释字并进行订正释读,对有误之处均给出释文,加按语阐明观点,总结出横向归纳形近字间区别性特征、纵向归纳部件演变规律、联系释例和上下文语境及综合运用等考释简牍草书文字的方法。白军鹏、汪云龙《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订补(六则)》[⑨]对马圈湾汉简中释字有问题的六枚简牍进行重新考释,订正新释简中“窳”“苣”“寂”“功”“肩”“眉”等字,并对与之相关的历史及文化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袁金平、卢海霞《敦煌马圈湾汉简“埻道”释义辨正》[⑩]根据汉简有关“埻道广、高各丈”的描述,在考察居延汉简相关简文中“埻”“埻![]() ”“射埻”等词的释义后,认为“埻道”非靶场,可指称箭靶,但在具体词义指向上,偏指用于射箭的土垛或土墙。李洪财《敦煌马圈湾汉简草书释正》[11]以《集释》为底本,对马圈湾汉简中草书九处误释字做了释读补证,指出“厶”在草稿中不一定只是代称,不仅在日常书写中,而且在上奏文书中已作为一种谦称使用。
”“射埻”等词的释义后,认为“埻道”非靶场,可指称箭靶,但在具体词义指向上,偏指用于射箭的土垛或土墙。李洪财《敦煌马圈湾汉简草书释正》[11]以《集释》为底本,对马圈湾汉简中草书九处误释字做了释读补证,指出“厶”在草稿中不一定只是代称,不仅在日常书写中,而且在上奏文书中已作为一种谦称使用。
(三)单字词考证、名物专题考释
秦凤鹤《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校读记》[12]根据《集释》公布的红外线图版和释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校读马圈湾汉简17条释文。张俊民《马圈湾汉简释文校释之一》[13]在前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集释》存在分歧的15例释文问题作以阐释。陈雨菡《敦煌马圈湾出土医简及“白椟带”再释读》[14]参用《敦煌汉简》释文图版,选取16枚马圈湾出土涉及疾病、医药内容的简牍,通过对戍卒疾病、马病、医方等简文内容释读,提供了研究汉代烽燧医事及其他社会情况的重要材料和依据,考证出药名“白椟带”当为“白朴叶”。张俊民《马圈湾汉简几组与西域有关文字的释读问题》[15]通过将两个近似的字进行辞例和图像排比、对照的方法,对马圈湾汉简“还沙”“虏政”“若绝城”等6例与西域有关的文字进行释读,肯定该方法的释疑作用,为汉代中外关系史料提供了重要补充。白军鹏《马圈湾汉简“焦党陶圣”章释文、性质及人名互证研究》[16]对马圈湾汉简“焦党陶圣”章木觚释文进行全面检视,对几处与字形相关的问题作以补充说明。从三方面论证木觚习字之用的性质,同时以《汉书》、汉印及汉简为准,将“焦党陶圣”章30个名字分为“汉人常用之名”“汉人不常用之名”“汉人稀用之名”及“其他” 四类。
(四)补释情况
刘乐贤《敦煌马圈湾出土药方简补释——为纪念谢桂华先生而作》[17]讨论马圈湾汉简中到底有多少支药方简的问题,认为至少有第505号、第563号(正、背面)、第 564号及第1177+1060号等4支残简,并依次对残存的“蜀署”“厚付”“白元”等药名进行释读。刘乐贤《敦煌马圈湾汉简第122号、133号补释》[18]以《集释》图版为依据,将马圈湾汉简反映王莽时期西域战事文档中第122号、133号分别释读为“戊部孤单,粮食、货财尽,兵器败伤,箭且索”“□□□□□□败,矢索,无以复战,货财、谷食单(殚)尽,车师因为共奴所”,认为2条简文描述内容密切相关,但稍有不同,前者为将要弹尽粮绝而面临战败,后者为已经弹尽粮绝且已经战败。张俊民《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辞例补释》[19]通过辞例资料对照的方式,对医药简、贳卖衣财物爰书、书信用语、簿记类文书、邮书刺(过书刺)等五方面共30例存在问题的释文进行纠正与补充。
二、语言文字研究
马圈湾汉简作为汉语史研究语料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以下从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作以梳理。
(一)上古语音系统探讨
随着马圈湾汉简的出土,新的通假字数量越来越多,为学界利用其研究上古音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新见通假字通释》[20]依据唐作藩先生《上古音手册》和文字考释等相关研究成果,对马圈湾汉简47个未见于其他文献或未被相关工具书收录的新见通假字逐一进行分析解释,为上古语音相关问题研究补充了新材料。周慧敏《<敦煌马圈湾汉简>谐声关系与上古声母研究》[21]在整理马圈湾汉简谐声字、制作谐音层级表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各声母间的音理关系,讨论其所反映的上古声母系统,认为至少存在23个单声母,具有端知章合并、精庄合并、群匣合并、云匣分立、存在日母及复辅音的特征,总体上谐声关系与已知成果保持一致,晓母与禅母、日母和心母、以母与精母三组特有声母关系比较密切,论文为上古声母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佐证和补充。
(二)汉简用字特征考察
汉字构形学、字体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使得马圈湾汉简有关用字研究逐渐丰富,内容多涉及用字断代研究、归纳字形与音义的对应关系及用字规律,是了解当时文字使用状况的重要途径。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简化字及其汉字学价值考》[22]统计出马圈湾汉简草书简化字79个,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存在四种简化方式,在与相应繁体字使用频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认为这种书写简化形体在当时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同时在为现行简化字提供直接字形来源、作为驳斥反对使用简化字而提倡恢复繁体字主张证据、完善相应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汉字学价值。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通假字系统量化研究》[23]从汉字应用史断代角度出发,对105个分析考察出的马圈湾汉简通假借字与本字语音及形体关系类型和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反映出其通假字在秦代书同文政策影响下趋于规范的社会地位。作者在出土文献通假字及汉代西北边塞地区用字特征研究上做出重要参考贡献。文字编是研究文字形态的重要资料,在汉代文字、汉字发展史研究方面有独特作用。赵丹丹《敦煌马圈湾汉简文字编》[24]在甄别各家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圈湾汉简文字进行统一分类整理,以《说文》十四卷为序排列,标注字形出处并附以词例,未释读文字也收于附录,为今后汉简各方面整理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文字材料。柳洋、周王嘉宇《由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看部分文字的类化讹写规律》[25]将马圈湾汉简在内已公布的西北汉简及其他汉简与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作横向比较,通过对比秦隶及后世魏晋俗字来探求源流,研究“类化讹写”的相关规律。
(三)词汇语法规律探求
马圈湾汉简关于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不多,只见两篇硕士论文讨论辞书订正和补语演变的问题。一是李蒙蝶《秦汉简帛中补语的语法形式和语义类型》[26]主要描写了包括马圈湾汉简在内的18种秦汉简帛中补语的语法形式和语义类型,并对秦汉简帛中补语整体面貌、补语前介词显隐、“动词+名词宾语+名词补语”结构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二是冯淑雅《<古辞辨>订补——以汉代简帛材料为中心》[27]以《集释》《敦煌汉简校释》等材料为中心,围绕词语使用地域、词语搭配、使用时代、词语系统义与指称义等方面对《古辞辨》进行订正,围绕补充构组成员、相关语义、词语搭配、词语所指、使用时代和辞例等方面进行补考,深入挖掘汉代简帛文献在汉语词汇史和辞书学上的重要价值。
三、史料考证补充
莫府档案是马圈湾汉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涉及汉末新莽时期西部防御、中原及西域周边国家的关系交往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专题,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化、制度程序打开新视野,证实传世文献记载,弥补文献不足。
后晓荣、苗润洁《关于敦煌马圈湾汉简涉及西域战争的几个问题》[28]对马圈湾汉简中涉及王莽时期西域战争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和考证,包括战争开始时间、失败原因、双方组成、《匈奴传》未记载匈奴参战等方面。刘俊《马圈湾汉简所见匈奴南将军史事发微》[29]通过梳理马圈湾遗址第五号探方所出约100余枚简文内容,补充完善传世文献对南将军逐步驱逐新莽势力出西域历史细节记载不足的情况,并溯源南将军称谓、设置时间、驻牧地迁移的问题,探究南将军在西域的崛起和失势,以期深化对南将军的认识。王子今《说敦煌马圈湾简文“驱驴士”“之蜀”》[30]讨论马圈湾汉简“驱驴士”“之蜀”内容出处、历史记录、文物遗存等内容,反映出汉代河西地区军事控制、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张俊民《驿路豹斑:西汉末年汉与西域间的政令传递》[31]主要解读513号简在当时制度有规范邮驿路线和没有具体邮驿机构时传递方式的具体情况,认为是汉代重要传递方式厩置驿骑行的又一种方式,为我们认识西汉末年邮驿和社会生活状况提供重要信息。李丽红《西北汉简所见省作制度研究》[32]整理马圈湾汉简中的省作简,对其省作人员构成、劳作内容、监管、后勤保障等情况进行讨论,整理分析省作简中出现的简册,是对马圈湾汉简省作制度的整体研究。李亚军《河西汉塞出土“人面形木牌”研究》[33]对马圈湾烽隧遗址出土9件“人面形木牌”功能从存在时间、出土地点、使用者三个方面进行辨析,对其中较为完整的1件尝试分类,认为“人面形木牌”是河西边塞地区戍卒用来镇宅护主、驱除灾祸的一种巫术工具。
四、书法理论临创实践
马圈湾汉简的文书草稿,书者率性而为,书体别具风格,是研究当时草书书法的第一手材料,研究者多从理论研究和临创实践的角度,分析马圈湾汉简文字的书法艺术风格及审美特点。
(一)书法基础文献参考
张德芳、王立翔主编《敦煌马圈湾汉简书法》[34]选取其中精佳者分类编排,放大精印,是研究和临习书法艺术的重要著作资料。柳洋、房俊贤《四体皆盛——<敦煌马圈湾汉简书法>对书法学习的意义》[35]从书法风格和用笔细节两大方面对该书书法学习的意义细致梳理讨论,认为其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研究参考价值极高,也预示着简牍书法研究向前迈了一大步。
(二)字体技法特征分析
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字体特征及其书法价值》[36]把马圈湾汉简文字字体分为汉篆、古隶、汉隶、草书和行书等五种类型,认为隶意风格存在于各种字体、草书已占据主体地位及过渡性字体被广泛使用是文字使用的典型特征。戴裕洲《秦汉习字简牍研究》[37]对马圈湾汉简发现共14枚习字简重新释读,按内容对其分类,分析书体特征,对主要书写者和书写目的进行探究,重点对习字简反映的习字方法进行解析。李洪智、高淑燕《从简牍特殊字样看汉代的书写文化——以敦煌马圈湾汉简为例》[38]对马圈湾汉简有别于常规书写的八分、隶行、隶草及这三种字体之外的其他字体书写字迹进行分析,忠实地反映出西汉后期至新莽时期近一百年间的汉字书写面貌。崔世芳《从马圈湾<王骏幕府档案简>看经典章草技法的形成》[39]立足于文字学和书法史研究角度,通过分析马圈湾《王骏幕府档案简》的草法、用笔、结体,将其与《月仪帖》《急就章》作对比,探究标准章草书体的形成和衍变轨迹,对传世经典章草技法的形成起到铺垫作用。蒋俊文《从<平复帖>及同类型简牍草书的临摹论及我的章草创作》[40]发掘借鉴与《平复帖》同类型的马圈湾汉简草书,从中探索章草临摹创作的元素和技法,增强笔者自身创作能力的同时,为当代章草的研习与创作提供新的思路与内容。
(三)特色书写文化探寻
李逸峰《敦煌草书简书写文化考察——以马圈湾汉简为中心》[41]通过对马圈湾汉简中草书书写形态、用笔情况及布局结字等情况考察,总结出当时草书符号已具备较高的统一性、规范性及艺术性,一定程度上是汉字书写隶变与草化的结果。王晓光《马圈湾等汉简看两汉之交时书用体及其他》[42]以列举马圈湾汉简中隶书、草书及其他用体的书写特色,分析其所处时期隶书书写特征,并将其草书与同近期的几种简牍草书做比较,指出两汉之交实用草书形态及其后草书发展情况,简论马圈湾汉简及汉代日常书写中古体、装饰性隶书及其他典型性写法的特征,并简要探讨了马圈湾汉简中草稿、书名具名等问题。孙嘉敏《马圈湾汉简书写研究》[43]通过分析隶书、篆书、新隶体,草书的笔法、结构、线质、章法及艺术风格,反映出西汉宣帝至新莽时期字体在马圈湾烽燧书写过程中运用情况。要文慧《简牍墨迹中隶书楷化书写考察——以转折笔形为例》[44]以转折笔形为中心,选取马圈湾汉简图版清晰的隶书简样本及《真草千字文》部分楷书辅助样本,通过量化分析对比,探讨转折笔形在数量、置向、方圆、粗细、长短等方面的变化,来考察其书写状况及找出楷化规律。
结 语
综上所述,2016-2023年敦煌马圈湾汉简的研究,主要偏重于释文辨识校正、书法理论临创实践方面,语言文字研究和史料考证补充方面的成果基本相当。相较于同时期发表的居延新简,及数量更多的悬泉置汉简乃至整个西北汉简,马圈湾汉简研究热度不高,主要因为简牍实物和图版保存状况不好、不清晰,使得以此为基础不断更新的研究还留有许多斟酌之处。
自《集释》高清图版再次亮相后情况大为改善,加之草书字体在马圈湾汉简中很常见,大部分学者除了关注释文商榷与再释读,多涉及到书法艺术研究部分,研究进度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当然,也存在将简牍主要涉及的内容作为研究重点,成果既不集中也不多见的情况,比如有关边关屯戍活动、管理程序及中外交往等问题。马圈湾汉简研究在具体问题上讨论多,但对其在总体把握和宏观研究上有所欠缺,较少形成体系研究。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公布,马圈湾汉简的释读研究需要和其他各地简牍材料结合起来佐证、比勘,需要简牍学者潜心积累、沉淀,如此既可开拓思路,又有助于在一些滞凝的问题上获得新的启示,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佉卢文文献所见汉晋鄯善国史研究”(21XZS016)。
作者简介:王玉婷(1998-),甘肃临潭人,文学硕士,甘肃简牍博物馆助理馆员,主要从事汉语史、简牍整理与研究。韩树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学》主编,主要从事敦煌学、法律社会史、西域史研究。
[①]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概述》,《中国书法》2019年第3期,第26-41页。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③]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
[④] 白军鹏:《敦煌汉简整理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⑤] 白军鹏:《敦煌汉简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⑥] 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
[⑦] 张丽萍、王丹:《<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未释疑难字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第95-98页。
[⑧] 张丽萍、张显成:《<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释读订误》,《简帛》第十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5-184页。
[⑨] 白军鹏、汪云龙:《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订补(六則)》,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七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6-171页。
[⑩] 袁金平、卢海霞:《敦煌马圈湾汉简“埻道”释义辨正》,《敦煌研究》2019年第6期,第82-87页。
[11] 李洪财:《敦煌马圈湾汉简草书释正》,《出土文献》2021年第3期,第65-70页。
[12] 秦凤鹤:《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校读记》,《中国文字研究》2018年第1期,第94-97页。
[13] 张俊民:《马圈湾汉简释文校释之一》,白云翔、王辉主编《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55-160页。收入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81-289页。
[14] 陈雨菡:《敦煌马圈湾出土医简及“白椟带”再释读》,《丝绸之路》2017年第6期,第16-18页。
[15] 张俊民:《马圈湾汉简几组与西域有关文字的释读问题》,《敦煌研究》2020年第5期,第27-32页。收入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322-332页。
[16] 白军鹏:《马圈湾汉简“焦党陶圣”章释文、性质及人名互证研究》,《出土文献》2021年第1期,第121-131页。
[17] 刘乐贤:《敦煌马圈湾出土药方简补释——为纪念谢桂华先生而作》,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六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6-213页。
[18] 刘乐贤:《敦煌马圈湾汉简第122号、133号补释》,《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十辑,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第42-49页。
[19] 张俊民:《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辞例补释》,敦煌市博物馆编《第二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20年,第115-126页。收入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90-307页。
[20] 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新见通假字通释》,《西部学刊》2017年第7期,第32-37页。
[21] 周慧敏:《<敦煌马圈湾汉简>谐声关系与上古声母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22] 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简化字及其汉字学价值考》,《励耘语言学刊》2017年第2期,第288-299页。
[23] 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通假字系统量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5期,第82-88页。
[24] 赵丹丹:《敦煌马圈湾汉简文字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25] 柳洋、周王嘉宇:《由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看部分文字的类化讹写规律》,《中国书法报》2022年8月30日第6版。
[26] 李蒙蝶:《秦汉简帛中补语的语法形式和语义类型》,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27] 冯淑雅:《<古辞辨>订补——以汉代简帛材料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28] 后晓荣、苗润洁:《关于敦煌马圈湾汉简涉及西域战争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05-111页。
[29] 刘俊:《马圈湾汉简所見匈奴南将军史事发微》,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二二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97-308页。
[30] 王子今:《说敦煌马圈湾简文“驱驴士”“之蜀”》,《简帛》第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97-210页。
[31] 张俊民:《驿路豹斑:西汉末年汉与西域间的政令传递》,《陇右文博》2020年第2期,第9-17页。收入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308-321页。
[32] 李丽红:《西北汉简所见省作制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33] 李亚军:《河西汉塞出土“人面形木牌”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4] 张德芳、王立翔主编:《敦煌马圈湾汉简书法》(全三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
[35] 柳洋、房俊贤:《四体皆盛——<敦煌马圈湾汉简书法>对书法学习的意义》,《书与画》2022年第10期,第62-67页。
[36] 雷黎明:《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字体特征及其书法价值》,《中国书法》2019年第6期,第77-83页。
[37] 戴裕洲:《秦汉习字简牍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38] 李洪智、高淑燕:《从简牍特殊字样看汉代的书写文化——以敦煌马圈湾汉简为例》,《西泠艺丛》2020年第5期,第2-7页。
[39] 崔世芳:《从马圈湾<王骏幕府档案简>看经典章草技法的形成》,《书法教育》2021年第10期,第27-33页。
[40] 蒋俊文:《从<平复帖>及同类型简牍草书的临摹论及我的章草创作》,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41] 李逸峰:《敦煌草书简书写文化考察——以马圈湾汉简为中心》,《中国书法》2019年第3期,第76-101页。
[42] 王晓光:《由马圈湾等汉简看两汉之交时书用体及其他》,《中国书法》2019年第3期,第42-75页。
[43] 孙嘉敏:《马圈湾汉简书写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44] 要文慧:《简牍墨迹中隶书楷化书写考察——以转折笔形为例》,《西部文艺研究》2022年第3期,第157-166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9月1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9月21日
点击下载附件: 2466王玉婷、韩树伟:2016—2023年敦煌马圈湾汉简研究综述.docx
下载次数:17
Copyright 2008-2018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35774号 地址: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200433
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總訪問量:9358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