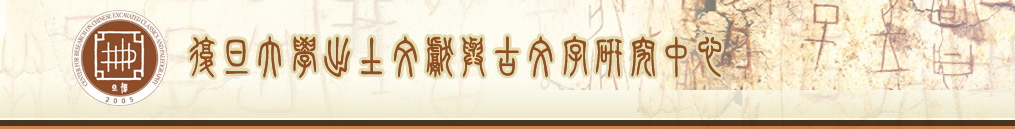
《多方》“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新解
(首發)
張懷通[①]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北石家莊,050024)
摘要:《多方》第一个“王若曰”领起段落中有一组用五个“劝”作结的文句,这个“劝”字都应校正为“观”,是观察的意思。与《康诰》中“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的含义相同,都是强调说明审理案件、处置刑罚时要多观察,冷静谨慎,以使判决适当。这体现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与《君奭》、《封许之命》、《昭后》中的“观德”观念,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提升了西周时代以“德”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思想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多方》 《康诰》 《君奭》 《封许之命》 《昭后》
《尚书·多方》第一个“王若曰”领起的周公讲话中有一组用“劝”作结的文句,其主题是“明德慎罚”,因此本文就采取借代的修辞手法,用“明德慎罚亦克用劝”来代替这组文句。为了便于讨论,现将其抄录于下。
乃惟成汤,克以尔多士,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②]
周公该段讲话的大意是,表彰商代从开国之君成汤,到亡国之君纣王的父亲帝乙,历代商王以“明德慎罚”为指导思想来治理国家的光辉事迹。多数字词的意思较为明显,文句的逻辑关系也较为顺畅,没有对理解文意造成障碍。然而其中一连出现五次的“劝”字,似乎有些问题。该字是常见字,一点也不生僻,但要在上下文中对之作出贴切解释,可能又很难。面对这个问题,学者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阙疑,不予解释,例如杨筠如先生[③]。这种做法较为谨慎,但回避问题,终究不妥。二是照着字面意思来讲,例如刘起釪。刘先生释“劝”为劝勉[④],这是继承了伪孔传的“劝善”、吕祖谦的“劝导”、“劝化”的观点[⑤]。然而,这个解释与文本时代、上下文意不协。首先,《多方》成篇的商周时代,“劝”字尚未出现[⑥],劝勉、勉励的意思用“蔑”来表达[⑦]。其二,劝勉既用于“要囚殄戮多罪”,也用于“开释无辜”,修饰说明的对象有明显矛盾,不可调和。吕祖谦说:“商传世之君,德固有深浅,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教化劝导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劝民。赦而民劝之犹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劝,则有默行于刑赦之间者矣。……每语结之以‘劝’者,天下非可驱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劝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维持长久之道也。”[⑧]吕氏极力自圆其说,乃至骋臆想像,但司法实践中的“默行”,或可使劝勉滥用,如此则有徇私枉法的嫌疑。这必定不是周公讲话的真实含意。为此,需要我们另辟蹊径,为这五个“劝”字,作出符合周公思想的新解释。
“劝”与“观”的通假
对于《多方》中这五个“劝”字的正确解释,需要古文字整体释读水平的提高。近来李守奎先生对于《尚书·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⑨]一句话的考释,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契机。
《君奭》这句话中的“劝”字,无疑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词语,而在“劝”前面起修饰作用的“割”与“申”二字,则是正确解释“劝”字含义而需要着力辨析考察的两个关键词语。割,郭店简《缁衣》引作“ ”,从刀从戈,意义相同。二者的字根是“害”,西周金文中的“害”可训为“大”。《礼记·缁衣》引作“周”,是因“害”与“周”形近而讹。申,《礼记·缁衣》引作“田”,郭店简《缁衣》引作“
”,从刀从戈,意义相同。二者的字根是“害”,西周金文中的“害”可训为“大”。《礼记·缁衣》引作“周”,是因“害”与“周”形近而讹。申,《礼记·缁衣》引作“田”,郭店简《缁衣》引作“ ”,都是由西周时代的“
”,都是由西周时代的“ ”简化假借而来,其本义是重复、反复、频繁。“劝”,《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都引作“观”。“劝”与“观”都从“雚”,可以通假,而以“观”为正字,其含义是观察、审视。为此,李守奎先生阐述三点理由:“第一,目前所见古文字中‘观’字习见,西周就已出现。‘劝’字罕见,且出现很晚,直到战国楚简才发现。‘观’的可能性大。第二,‘观德’成词,古人习语。……第三,‘观德’是西周人的重要观念。上帝在天上的帝廷,监临下土,观人之德,有其德则授之天命,受命者即为天子。天命可以变革,无其德则失其命而为诸侯、为庶人,是谓‘革命’,这是一套自洽的理念。‘观德’是受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因此《君奭》“昔在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一句话可以校正为:“昔在上帝害申观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其大意是:“往昔上帝隆重地频频地观察文王之德,因其合于帝心,便降大命于文王之身”[⑩]。李先生的校订与考释,深入细致,正确可从。
”简化假借而来,其本义是重复、反复、频繁。“劝”,《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都引作“观”。“劝”与“观”都从“雚”,可以通假,而以“观”为正字,其含义是观察、审视。为此,李守奎先生阐述三点理由:“第一,目前所见古文字中‘观’字习见,西周就已出现。‘劝’字罕见,且出现很晚,直到战国楚简才发现。‘观’的可能性大。第二,‘观德’成词,古人习语。……第三,‘观德’是西周人的重要观念。上帝在天上的帝廷,监临下土,观人之德,有其德则授之天命,受命者即为天子。天命可以变革,无其德则失其命而为诸侯、为庶人,是谓‘革命’,这是一套自洽的理念。‘观德’是受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因此《君奭》“昔在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一句话可以校正为:“昔在上帝害申观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其大意是:“往昔上帝隆重地频频地观察文王之德,因其合于帝心,便降大命于文王之身”[⑩]。李先生的校订与考释,深入细致,正确可从。
李守奎先生的校订与考释,可以得到清华简《封许之命》与《昭后》的验证。
清华简《封许之命》:……越在天下,故天劝之亡斁,尚纯厥德,膺受大命,骏尹四方。[11]
清华简《昭后》:昭后元年,乂辟员旧,一日壬辰赏罚。十有一祀,以猷丕休,延及宠子。天劝甚申,厥德有止。[12]
《封许之命》是一篇成王封建吕丁于许建国的诰命。所引文句的内容,如同其他周初封建诰命一样,讲的是文王有德而接受天命的时代政治主题。其中的“劝”应是“观”,即观察、审视。“亡斁”,即无厌、无穷无尽。这是反说,正说则是重复、频繁,即“申”。“观”与“德”前后照应,近于成词“观德”,是西周习见的思想观念。这句话后半部分的含义与《君奭》大体相同,大意是:上天反复观察审视文王,文王道德纯正,因而接受天命,治理天下[13]。
《昭后》记载的是“周昭王即位,赏罚员旧,延及宠子,以谋丕休”的史实[14]。其中的“天劝甚申,厥德有止”一句话,既与《君奭》照应,也与《封许之命》照应。“劝”即“观”,即观察、审视。“申”,即重复、频繁。“观”与“德”前后照应,近于成词“观德”。该句大意是:上天反复观察昭王,昭王道德恰如其分[15]。
清华简《封许之命》与《昭后》验证了李守奎先生对于《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的校读完全正确,这就为我们重新解释《多方》中包含了五个“劝”字的段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康诰》看《多方》“明德慎罚亦克用劝”
《多方》中的五个“劝”字,应该依照《君奭》、《封许之命》、《昭后》中“劝”校正为“观”之例,也都校正为“观”。如此一来,以“观”作结的五个文句的大意是:成汤慎用刑律,观察;施民刑罚,观察。直到帝乙的历代商王,无不明德慎罚,观察。囚禁杀戮罪犯,也观察。释放无罪人员,也观察[16]。此处的意译只考虑“信”,如果加上“达”与“雅”,则“观”字应译为观察、慎思、明辨。这才是周公的完整的原本意思。
在施行刑罚的过程中,时时处处观察,小心谨慎办理,不仓促行事,以使案件量刑适当,使涉案人员得到公正对待。这样的审慎态度与严谨作风,体现了周公一贯的政治法律思想。首先,看同篇《多方》。《多方》第二个“王若曰”领起段落中有句云:
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17]
其中的“至于再,至于三”是后置状语,强调说明的是“告教”与“要囚”的审慎态度。“要囚”是《多方》两个段落共有的词语。一而再、再而三地“告教”、“战要囚”,当然包涵了“观”或“害申观”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对应的正是“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
再次,看《康诰》。《康诰》是周公封建康叔于卫建国的诰命。在讲话中,周公嘱咐康叔行使政令应执行的原则与掌握的分寸时说:
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18]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19]
先看第一段引文。这段今译是:“如果有人犯了小罪而不是无心的过失,且永远恃恶不改;那是他自己(有意)去做不法的事;像这样的,他的罪恶虽小,也不可不杀他。如果有人犯了大罪而不是永远恃恶不改,而且是因无心的过失偶然遭到罪过,既已惩罚了他的罪过,像这种人就不可杀死他。”[20]这是周公对于自己刑罚思想的详细论述。周公认为,审理案件应掌握的原则是,从外部说,罪分大小,罚分轻重;从内部说,动机分有意无意,态度分改与不改;宗旨则是“敬明乃罚”。如此慎重严谨地对待案件,体现的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观”字,观案,观人,观心,观动机,观效果,也就是《多方》的“慎厥丽乃劝【观】;厥民刑用劝【观】”。
再看第二段引文。这段今译是:“要监禁罪犯,必须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天的时间,然后才叛定应否监禁。”[21]这是周公嘱咐康叔,对罪犯处以刑期,不要急于作出决定,应有一个冷静期,以便不为个人好恶、情绪起伏所左右,从而达到判罚适中的结果。这不就是上文辨析的《多方》第二个“王若曰”领起段落中的“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吗?这不就是本文探讨对象《多方》第一个“王若曰”领起段落中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吗?
看《梓材》。《梓材》是由周公分别对康叔与成王的两次讲话编联合成的篇章,两次讲话的时间大约与《康诰》、《酒诰》紧密相连。在对康叔的讲话中周公阐述了自己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
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击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22]
这段引文的意思有些隐晦,蔡沉说:“此章文多未详。”[23]这是较为诚实的态度,值得肯定。但由开头的“予罔厉杀人”,以及后两句结尾的两个“宥”字看,周公的大概意思是,向康叔表明自己处理刑事案件的原则,不滥杀无辜[24],以及宽宥一些因忠君而杀人伤人者。这个意思与《康诰》、《多方》所述“观”等具体做法稍微有些差异,但所体现的“明德慎罚”思想则一脉相承。
由《多方》内证与《康诰》(《梓材》)外证两方面看,《多方》的“明德慎罚,亦克用劝”段落中连续使用的五个“劝”,确实是“观”的通假字。正字应是“观”,其含义是观察、审视、慎思、明辨。
“观”与西周“明德慎罚”政治主题
《多方》与《康诰》(《梓材》)之所以在“劝【观】”字上相通,是因为基于一个共同的政法背景,那就是审理案件、处置刑罚。其指导思想,《多方》称之为“明德慎罚”,《康诰》称之为“敬明乃罚”,而在其他语境中,《康诰》还称之为“义刑义杀”等。相同的文句,相近的思想,原因在于《多方》与《康诰》(《梓材》)的发布者都是周公,而且都是发布于东征后的较短时间内。从《尚书》篇次上看,《多方》与《康诰》(《梓材》)间隔较远,而实际上却都是先后紧密相连、历史背景相同、思想观念相通的政治文诰[25]。
《多方》、《康诰》(《梓材》)与《君奭》、《封许之命》、《昭后》之所以在“劝【观】”字上相通,是因为审理案件、处置刑罚在西周时代是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既与现实政治的运作有关,也与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有关,因此在《多方》中“观”所体现的是与“慎罚”相辅相成的“明德”,在《康诰》(《梓材》)中是“敬明”,而“敬明”是道德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君奭》、《封许之命》、《昭后》中“观”与“德”前后照应,几乎形成“观德”的成词。从“慎罚”开始,经过“敬明”、“明德”,而上达天帝,由此西周最高统治者便把王权合法性牢固地建立在了天命的基础之上。
《多方》、《康诰》(《梓材》)中“劝【观】”的主体是刑罚的审判者,《君奭》、《封许之命》、《昭后》中“劝【观】”的主体是上帝。周公在《君奭》中将“观”与“观德”衔接起来,将“德”与“天命”衔接起来,向上与康诰》(《梓材》)、《多方》贯通,向下开启《封许之命》、《昭后》先河,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以“德”为核心内容的西周政治思想体系的理论水平。
行文至此,《多方》中以“劝【观】”作结的五个文句的意思已经阐明,现在以此为前提,对《多方》、《皇门》中几个带“劝”的文句的意思,尝试着作一推测。(1)《多方》“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道】”[26]。其中的“劝”应校正为“观”,“终日”是“申”即重复、频繁的意思。大意是,不能够频繁地观察天帝之道。(2)《多方》:“尔不克劝忱【信】我命”[27]。其中的“劝”应校正为“观”,大意是,你们不能够观察相信我的命令。这样的校正与解释,都与各自的上下文意协调。(3)《皇门》“克用有劝,永有孚于上下”[28];(4)清华简《皇门》“先王用有劝,以宾佑于上”[29]。这两个“劝”都应校正为“观”,都与同一语境中的“上下”或“宾”、“上”文法搭配,文意顺适。(5)《盘庚中》“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30];(6)《顾命》“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宏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31]。这两个“劝”也应校正为“观”。前者“思”与“观”相对,“灾”与“忧”相对;后者“柔”、“能”与“安”、“观”同义联用。放到语境中,也能够做到文通字顺,文意畅达。
总之,这些“尚书”篇章,反映了殷商西周时代有“观”,有“蔑”,但无“劝”的历史语言实际,当是可以肯定的。
[①] 张怀通,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先秦史、“尚书”学研究,倡导“尚书”源于礼仪说,倡议建立“尚书”学。
[②]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258页。
[③]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258页。
[④]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25页。
[⑤] 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页。
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⑥] 李守奎:《从文通字顺的西周之诰到佶屈聱牙的<尚书>——兼论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问题》,《湖北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⑦] 于省吾:《释“蔑 ”》,《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晁福林:《金文“蔑曆”与西周勉励制度》,《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⑧] 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⑨] 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4页。
笔者按:其中的“在昔”二字,《礼记·缁衣》引作“昔在”。这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因此引述相关文句时,依从作者的引用顺序。请读者明鉴。
[⑩] 李守奎:《从文通字顺的西周之诰到佶屈聱牙的<尚书>——兼论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问题》,《湖北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笔者按:李先生说:郑玄读“害”为“盖”,大概是当作语词不强作解释。但在自己校正的《君奭》文句中仍然将“害”用“盖”来替代。综合考虑上下文意,笔者采李先生“害”字说。请读者明鉴。
[1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8页。
[1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第92页。
[13] 笔者按:诰命开头缺失一支简,对于文意的理解造成不利影响,此处只是串解大意而已,未必十分准确。请读者明鉴。再,李学勤先生说:“雚,读为‘劝’,《说文》:‘勉也’,《广雅·释诂二》:‘助也。’”(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8页)这是沿用了传统思路,应予以纠正。
[1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第91页。
[15] 笔者按:马楠先生说:“雚,读为‘劝’。……‘天劝甚申,厥德有止’,类似《书·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此处谓上帝申劝昭后之德有所止。或说‘雚’读‘观’,谓上帝反复观昭后之德,其德有所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第93页)现在看来,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或说”。
[16] 笔者按:该段落中有两个关键字词的意义需要特地说明。(1)丽。“慎厥丽”之“丽”,及其前文的“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中的“丽”,笔者认为其含义是刑律,采纳的是杨筠如的主张。杨先生说:“丽,《吕刑》郑注‘施也’。按本书言丽,或为法则,或为刑律,皆不作施义。《吕刑》‘越兹丽刑并制’,又曰:‘苗民匪察于狱之丽’,与本篇下文‘慎厥丽乃劝’,丽,皆谓刑律也。其义与刑大同小别。《顾命》‘奠丽陈教’,与此文‘不克开于民之丽’,丽,皆谓法则也。《汉书·东方朔传》‘孝文皇帝之时,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丽与准对文,亦取法则之义。以声类求之,疑即后世之律令。丽之得转为律,犹骊之得转为黎也。古律黎同部,《广雅·释草》‘茟,藜也。’是其证。此文‘民之丽’,犹言‘民之则’。《诗·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是其义也。”见氏著《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56页。(2)要囚。要囚即幽囚,幽禁囚犯的意思。杨筠如先生说:“要囚,即幽囚之假。《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王先生释要为幽,是也。”见氏著《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258页。学者所作其他解释,不予采纳。请读者明鉴。
[17]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261页。
[18]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175页。
[19]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177页。
[20]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84页。
[21]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84页。
[22]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56页。
[23] 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56页。
[24] 曾运乾撰、黄曙辉点校:《尚书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25] 张怀通:《<尚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28-41页。
[26]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255-256页。
[27]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263页。
[28]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宋志英、晁岳佩选编《<逸周书>研究文献辑刊》第八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王念孙撰,徐炜君等校点:《读书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年,第36页。
[29]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64页。
笔者按:程浩说:“雚 从下文‘宾佑于上’来看,此字在简文中当读为‘观’。传世本作‘劝’,应是误读了‘雚’所假之义。”见氏著《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75页。程先生的判断正确可从。
[30]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109页。
[31] 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59年,第277 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11月1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11月17日
点击下载附件: 2486張懷通:《多方》“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新解.docx
下载次数:44
Copyright 2008-2018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35774号 地址: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200433
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總訪問量:9344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