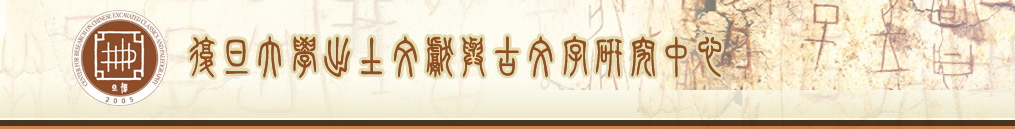
釋慈利楚簡中的“臨”字
吳冕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文物》1990年第10期圖版柒公佈有一幀慈利石板村36號楚墓出土竹簡的照片。其中一支簡的簡文可釋寫如下(此簡照片及我們所做的摹本見文末):
命戒▃,一鼓,前行 之,後行𡒊(舉)
之,後行𡒊(舉) (戟)▃。鼓
(戟)▃。鼓 武進□□□□▃□□□□[1]
武進□□□□▃□□□□[1]
此簡內容關於軍隊布陣和交戰,不見於傳世文獻,可能屬於一種兵書類古佚書。從前肖毅和魏宜輝都對此簡作過考釋,茲引二家說法如下:
【肖毅】释文为“□戒、一鼓前行□之后行举幾(?)、鼓□□进□鼓(?)□□、□□□□”。
“前行”后一字左侧所从与上博简《柬大王泊旱》简14  字同。[2]
字同。[2]
【魏宜辉】释文为:“命戒,一鼓:前行 之,後行𡒊(舉)
之,後行𡒊(舉) (戟)。鼓□武進□□□□金音□□□”。
(戟)。鼓□武進□□□□金音□□□”。
簡文“前行”後之“ ”字,肖文認爲其左旁與上海博物館藏竹書《柬大王泊旱》簡14第四字同。其説可從。關於上博簡中的“
”字,肖文認爲其左旁與上海博物館藏竹書《柬大王泊旱》簡14第四字同。其説可從。關於上博簡中的“ ”字,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暫無定論。
”字,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暫無定論。
“行”指战阵行列,《汉书·李广苏建传》就有“前行”、“后行”之语:“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军阵一般将盾安排在前方作防护,此处“前行 之”的“
之”的“ ”字可能有“遮蔽”之义。此言前列士兵持盾防护,后列士兵持戟备战。简文后段“鼓”“进”“金音”等内容也与《汉书》记载类似。[3]
”字可能有“遮蔽”之义。此言前列士兵持盾防护,后列士兵持戟备战。简文后段“鼓”“进”“金音”等内容也与《汉书》记载类似。[3]
兩位學者都將慈利簡的 字左側所从與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的
字左側所从與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的 字相聯繫。而不難看出二者構形完全相同,皆从人从口,口在人“臂”下方。因此將兩個字形貫通起來討論,很有必要。關於上博簡
字相聯繫。而不難看出二者構形完全相同,皆从人从口,口在人“臂”下方。因此將兩個字形貫通起來討論,很有必要。關於上博簡 字的釋讀,學界多有討論,其中何有祖《釋〈簡大王泊旱〉“臨”字》的觀點值得注意。其指出,
字的釋讀,學界多有討論,其中何有祖《釋〈簡大王泊旱〉“臨”字》的觀點值得注意。其指出, 字與楚文字“臨”字
字與楚文字“臨”字 的偏旁
的偏旁 形同,是“臨”字的省寫。又認為
形同,是“臨”字的省寫。又認為 可能是“臨”的聲符,因為楚文字“臨”所从的
可能是“臨”的聲符,因為楚文字“臨”所从的 形可以是三個(如
形可以是三個(如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簡1);也可以是兩個(如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簡1);也可以是兩個(如 ,上博五《弟子問》簡9);還可以是一個(如
,上博五《弟子問》簡9);還可以是一個(如 ,馬王堆《陰陽五行甲本》行138)。由此推斷,
,馬王堆《陰陽五行甲本》行138)。由此推斷, 應該是“臨”字的基本聲符。比較直接的例子就是同樣屬于《弟子問》簡9的“臨”字也可省作
應該是“臨”字的基本聲符。比較直接的例子就是同樣屬于《弟子問》簡9的“臨”字也可省作 。因此可以將《柬大王泊旱》中的
。因此可以將《柬大王泊旱》中的 直接釋為臨。[4]
直接釋為臨。[4]
我們認為,將 視為“臨”的省寫(或者說截除性簡化)比較好。而慈利簡的
視為“臨”的省寫(或者說截除性簡化)比較好。而慈利簡的 字可分析為从
字可分析為从 从頁,很可能是在截除簡化而來的
从頁,很可能是在截除簡化而來的 字基礎上又加注意符“頁”,從而產生的“臨”的後起形聲字。
字基礎上又加注意符“頁”,從而產生的“臨”的後起形聲字。
慈利簡“前行 之”中的
之”中的 應當用為動詞,指前列士兵的動作。前引魏宜輝文將此字推測為“遮蔽”之意,大概正是由這種判斷出發的。不過從字形本身看,魏說沒有很好的依據。而若將此字釋為“臨”,則不但與字形相合,而且放在該簡文例中,也很通順。
應當用為動詞,指前列士兵的動作。前引魏宜輝文將此字推測為“遮蔽”之意,大概正是由這種判斷出發的。不過從字形本身看,魏說沒有很好的依據。而若將此字釋為“臨”,則不但與字形相合,而且放在該簡文例中,也很通順。
先秦秦漢兵書中常見“臨敵”一語,為與敵軍交戰之意。如《吳子·論將》:“果者,臨敵不懷生”[5];《六韜·立將》:“臨敵決戰,無有二心”[6];《淮南子·兵略》:“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7];又《尹文子》述越王句踐報吳之事,亦言:“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8]。慈利簡“前行臨之”的“之”所指代的對象應當是敵軍,則“臨之”亦猶兵書中常見的“臨敵”,指交戰。簡文“前行臨之,後行舉戟”,大意是前列士兵與敵軍交戰,後列士兵舉戟準備接續進攻。
綜上所述,此簡 字从頁、
字从頁、 (臨省)聲,應當釋為“臨”。楚簡字形中可與之聯繫的還有清華十《四告》簡1的
(臨省)聲,應當釋為“臨”。楚簡字形中可與之聯繫的還有清華十《四告》簡1的 字。兩個字形的區別在於後者“頁”形下部所从是人旁而非卩旁,且後者多出一個攴形。楚文字中常有“頁”形所从卩旁與人旁互作之例,如郭店簡《語叢一》中出現的兩個“色”字
字。兩個字形的區別在於後者“頁”形下部所从是人旁而非卩旁,且後者多出一個攴形。楚文字中常有“頁”形所从卩旁與人旁互作之例,如郭店簡《語叢一》中出現的兩個“色”字 (簡13)、
(簡13)、 (簡110),就是前者从“卩”而後者从“人”。也可能是“卩”旁譌變為人旁和攴旁,因為《四告》字形中人旁腿部與攴旁上方筆畫之間恰成一封閉結構,類似卩形。
(簡110),就是前者从“卩”而後者从“人”。也可能是“卩”旁譌變為人旁和攴旁,因為《四告》字形中人旁腿部與攴旁上方筆畫之間恰成一封閉結構,類似卩形。
關於《四告》的 字,單育辰《清華十〈四告〉釋文商榷》已將它所从的
字,單育辰《清華十〈四告〉釋文商榷》已將它所从的 旁與“臨”字偏旁
旁與“臨”字偏旁 認同,並指出其當是“臨”之變體[9]。只是
認同,並指出其當是“臨”之變體[9]。只是 除人以外的部分不像典型的口形,單純從這個形體本身看,與臨字偏旁
除人以外的部分不像典型的口形,單純從這個形體本身看,與臨字偏旁 還有些許距離。因此後來又有學者認為此形當作別解,如王寧《讀清華拾〈四告一〉散札》就將此形釋為“包”,認為其中類似口形的部分不是口,而是反寫的“巳”形。[10]而現在我們既已將慈利簡
還有些許距離。因此後來又有學者認為此形當作別解,如王寧《讀清華拾〈四告一〉散札》就將此形釋為“包”,認為其中類似口形的部分不是口,而是反寫的“巳”形。[10]而現在我們既已將慈利簡 字釋為“臨”,就能為《四告》
字釋為“臨”,就能為《四告》 字釋“臨”之說提供很好的支持。
字釋“臨”之說提供很好的支持。
(順帶說一下這支慈利簡中的 字。此字以往學者未釋。我們懷疑此字上从网,下方所从的
字。此字以往學者未釋。我們懷疑此字上从网,下方所从的 是疋“象腓腸”的圈形部分與“止”形上方的兩筆共用筆畫而來的簡寫。疋當為此字聲符。
是疋“象腓腸”的圈形部分與“止”形上方的兩筆共用筆畫而來的簡寫。疋當為此字聲符。 可隸定為“
可隸定為“ ”。相同結構的字形還見於上博八《李頌》簡1:“摶外
”。相同結構的字形還見於上博八《李頌》簡1:“摶外 中”。此處
中”。此處 字當讀為“疏”,“鼓疏”即鼓點稀疏。)
字當讀為“疏”,“鼓疏”即鼓點稀疏。)
附图:

[1] 簡文原本帶有句讀符號,此處依原樣用“▃”號釋錄。
[2] 肖毅:《慈利竹書零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2006年,第330頁。
[3] 魏宜輝:《慈利楚簡校讀札記》,《古典文獻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2頁。
[4] 何有祖:《釋〈簡大王泊旱〉“臨”字》,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2月20日。鏈接:http://www.bsm.org.cn/?chujian/4739.html
[5] 陳曦:《吴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181頁。
[6] 《六韜》,《續古逸叢書》影刊宋武經七書本,卷三,第十八頁a。
[7]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19頁。
[8] 王啓湘:《尹文子校詮》,《周秦名家三子校詮》,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8頁。
[9] 單育辰:《清華十〈四告〉釋文商榷》,《佔畢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05頁。(這條考釋意見最初於2020年11月20日發表於簡帛網論壇“悅園”:《清華十〈四告〉初讀》評論第26樓。)
[10] 王寧:《讀清華拾〈四告一〉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1年8月10日。鏈接: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5801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10月2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10月24日
点击下载附件: 2480吳冕:釋慈利楚簡中的“臨”字.docx
下载次数:40
Copyright 2008-2018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35774号 地址: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200433
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總訪問量:939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