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少華、王華寶主編;[清]俞樾著、胡文波、白朝暉、張曉青、謝超凡、劉珈珈、王倩倩整理《春在堂雜文》出版
汪少華、王華寶主編;[清]俞樾著、胡文波、白朝暉、張曉青、謝超凡、劉珈珈、王倩倩整理《春在堂雜文》由鳳凰出版社於2021年12月出版,定價365元。以下是該書書影、前言及《俞樾全集》總目録。
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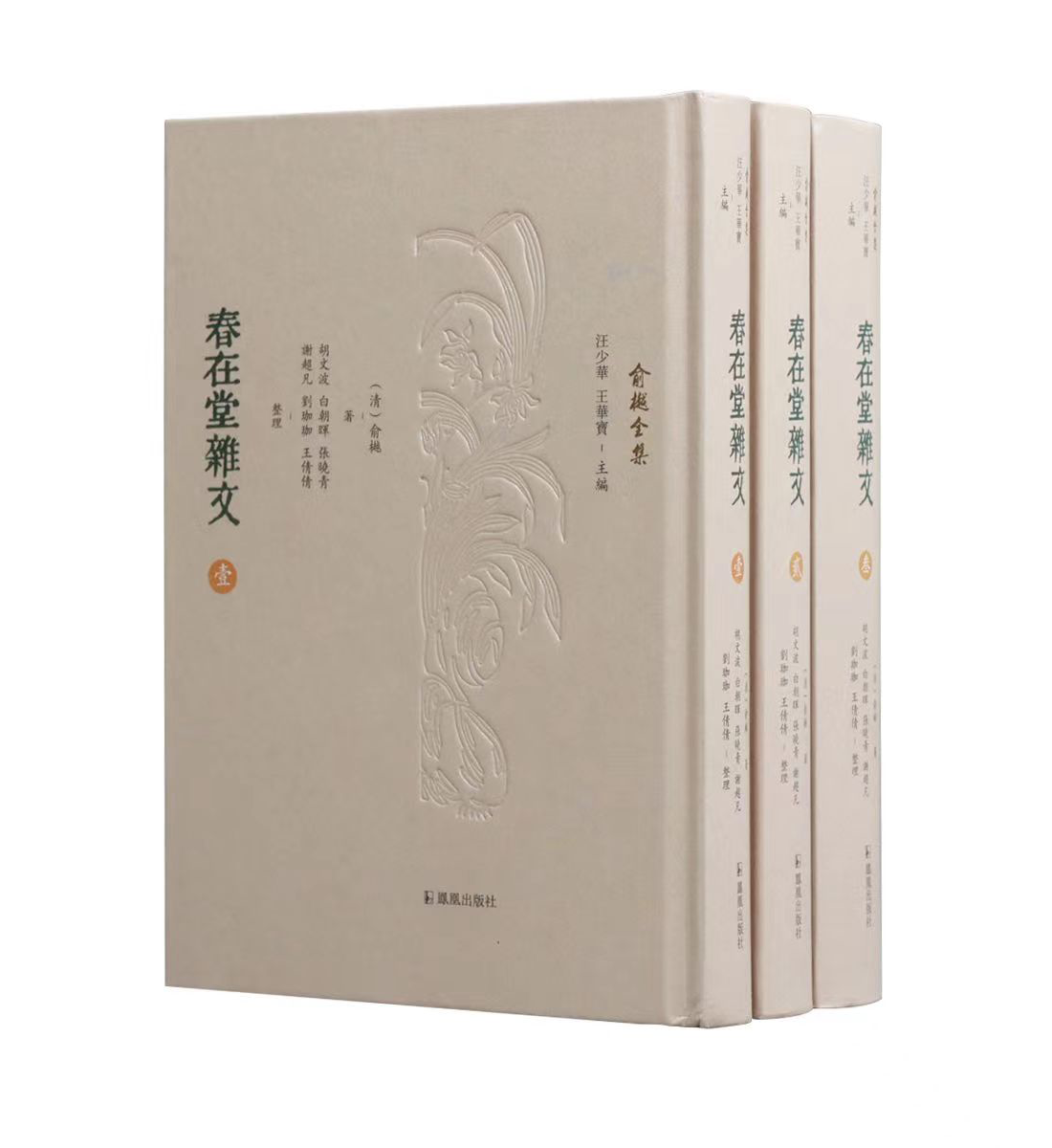
前言
一、俞樾與《春在堂雜文》
俞樾是晚清著名學者,生於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卒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七),字蔭甫,號曲園,是乾嘉漢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春在堂雜文》合計四十三卷、七百九十五篇,是俞樾中年以後文章的結集。其中多記、傳、序、跋之類,占其大半,其他如壽序、碑志、銘贊誄啓,不一而足,洵可稱雜文。
浙江德清縣的俞氏,號稱望族,但其實在俞樾之前所出人物並不多。俞樾的父親俞鴻漸,字儀伯,是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舉人,候選知縣,例授文林郎。著作有《印雪軒詩鈔》十六卷、《文鈔》三卷及《隨筆》四卷等。俞樾是俞鴻漸的次子。俞樾自幼隨母兄到杭州生活求學,其後如他的《汪蓮府兵部六十壽序》一文中所說“年十五侍先大夫讀書南蘭陵”,“初學舉子業”。後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中進士第十九名。殿試的詩題是《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首聯作:“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豔陽。”當清朝內憂外患漸起的時候,此詩極得主考官曾國藩激賞,認爲“他日所至,未可量也”。其後又爲其題匾額“春在堂”。俞樾對此事當然終身引以爲榮,對曾國藩的知遇之恩也可稱感激涕零。這在他的雜文中都歷歷可見。
近人對俞樾的歷史評價,首稱其經學,次稱其詩歌,最後是其文。詩歌成績從“花落春仍在”已可見一斑,暫不去說。爲文的成就,後面再說。而眾口稱讚的經學成就,當然是他最大貢獻。但從俞樾的一生來說,教書育人的貢獻,未必就比他撰作經學著作小。中進士後,改庶吉士。咸豐二年,授散館編修。五年,放河南學政。七年,他因爲任河南學政時科舉試題被御史劾奏“割裂經義”,罷官歸鄉。其後認清自身不見得適合仕途,先是杜門讀經,專心寫書,“比年撰述,已及八十卷”。中國傳統士大夫若仕途受阻無望,往往就轉向從撰著中實現自我價值,“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倘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與曾國藩函)於是有“曲園”之營建,曾國藩書額“春在堂”三字也掛到了曲園的主室之上(卷一《曲園記》)。但學不可孤,教書育人是士大夫社會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俞樾先後在蘇州紫陽書院、上海求志書院,在杭州詁經精舍時間最長,達三十餘年之久。他的學生中,有聲名者極多,《清史稿·儒林傳》所列舉的如:戴望、黃以周、朱一新、施補華、王詒壽、馮一梅、吳慶坻、吳承志、袁昶等。此外還有如日本學人,如章太炎等革命志士。《春在堂雜文》中關於書院教育的文章很多,卷一第一篇就是《重建詁經精舍記》,又有《紫陽課藝序》等。讀後可知,他是一位極佳的教育家。著書立說流傳後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兩者俞樾都極有建樹。另外,在東南凋敝之時,他提出浙江書局等刊刻二十四史和諸子之書,對後世的意義也很巨大。
《春在堂雜文》是俞樾的雜文集,他曾說:“余舊定《賓萌集》五卷,終於‘雜篇’。其後所作雜文日益多,遂別爲《春在堂雜文》。”(《賓萌集補篇小序》)可見《春在堂雜文》的緣起。而以“春在堂”爲名,則遠因“花落春仍在”之見賞曾文正公,又因“花落”之讖驗其仕途中斷,冀圖其文之可傳後世。俞樾在經學研究著作之外,雜文撰寫隨其年齡增長而增加,先是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辛未命人謄寫若干篇,而由學生付之剞劂,題作《春在堂雜文》,二卷。此後至光緒三十一年,三十餘年間雜文撰著“無月無之”(《春在堂雜文·序目》),遂將所作重爲編排,定爲初編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六編補遺六卷,總四十三卷。從撰著時間來說,雜文撰著貫通俞樾之一生,從未間斷。從篇幅卷帙來說,四十三卷共約七百九十五篇文章,足稱繁富。可以說,通過《春在堂雜文》,足可探究俞樾之一生,及其學問之大概。
二、尊德性而道問學:俞樾雜文之取法
中國古代的學者、士大夫,著述往往廣泛而龐雜,但皆有其思想底色。從經義研究,到詩文創作,到典籍整理,學者的思想底色是貫穿其中的。俞樾的雜文撰著貫穿其一生,最可見其思想底色。俞樾的學問,首先在於經學,其次在於諸子,而諸子之學又以經學爲歸屬。他的主張,其實在《春在堂雜文》初編卷一的第一篇文章《重建詁經精舍記》中就直接說明了:
學問之事,莫大乎通經。通經之道,義理尚矣。然義理不空存,必有所麗。……推文達之意,通經必從訓詁始。……使學者讀許、鄭之書,通曉古言,推明古制。即訓詁名物以求義理,而微言大義存其中矣。
可見,俞樾的主張同於阮元(謚文達)。學問之歸在於經學,通經以通曉其義理爲尚。而義理之通,端賴訓詁名物。如何訓詁,在讀許慎、鄭玄之書。這是乾嘉之學的路數。無論漢學、宋學,對於義理、訓詁都不會明言偏廢,而實際上則各有側重。乾嘉學派以考據爲長,重在糾宋人之偏,不談性理,而重訓詁。重訓詁,實際仍舊是爲求義理,而義理不能空談故也。他在《鄭氏佚書序》中說:“兩漢經師之學,至鄭君而集大成。每發一義,無不貫穿羣經。不知者以爲鄭君所臆造,而不知其按之羣經,如以肉貫丳也。典午之代崇尚清談,鄭學幾廢。幸唐人正義《禮》用鄭注,《詩》亦主鄭箋。高密之緒賴以不隊。元明以來空談心性,鄭學又微。本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士抱不其之經,户習司農之説。”明乎其言崇尚漢學,抵制兩晉與兩宋之學。
對於儒學,俞樾曾將其分爲六類:
自孔氏諸弟子各以其所學散處諸侯之國,原遠而末分,至於今益甚。有曰性理之學,則究性命、辨義利者也。有曰經世之學,則策富强、課農戰者也。有曰經籍之學,則窮訓詁、考制度者也。有曰載記之學,則志得失、鏡古今者也。有曰曆算之學,則精推步、測高廣者也。有曰詞章之學,則研聲律、儷青白者也。是數者各得其質之所近,各行其業之所習,彼此相笑而莫能通。(續編卷三《馮景庭先生顯志堂稿序》)
俞樾馬上引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如果不能貫通,則無用。如能夠貫通,則這些學問“固可得而一”。俞樾自身,是符合他所說的“有以貫之”的,他可稱爲一代通儒。與儒家之學分而爲六類相似的,雜文則無所不涉,其文體無一致之形。但其中有一以貫之的,即訓詁以求通經,因而經世致用。他稱歸有光“原本道德,根柢六經”,稱顧亭林之學“有體有用,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講求古音,發明古義,……無論言漢學、言宋學,而皆以先生爲一大宗。”(三編卷三《合刻歸顧朱三先生年譜序》)俞樾所稱頌的,即他所追求的,也正是四十三卷《春在堂雜文》之宗旨。
既然崇漢學抵宋學,則於孔子之理論,偏於禮之一端,離於仁之一端。但處於近世,遠於漢宋,秉承通儒之追求,俞樾又比較沒有門戶之見,主張“治經不專主一家之學”,亦知道“世謂漢儒專攻訓詁,宋儒偏主義理,此猶影響之談、門戶之見。其實漢儒於義理亦有精勝之處,宋儒於訓詁未必一無可取也。”雖然如此,其重點仍在於“漢儒於義理亦有精勝之處”,對宋儒之訓詁,僅僅是稍可取而已。
俞樾的漢宋分野觀,不是門戶之見,是從其經學、子學思想而來的。漢宋之分野,在中國思想史中有其內在理路,清儒之中,多崇荀子,而抑孟子。俞樾也尊荀抑孟[1]。首先看他的《荀子詩說》,即經學中對《毛詩》的重要研究:在《荀子诗说序》中,他将这一意图表述得非常明白:“按《經典釋文》:《毛詩》者,出自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六毛公。是荀卿傳詩,實爲《毛詩》所自出。……今讀《毛詩》而不知荀義,是數典而忘祖也。故刺取《荀子》書中引詩者凡若干事,以存荀卿詩說焉。”六經之中,《詩》爲關乎教化的極其重要的典籍,俞樾特將《毛詩》譜系梳理出,明確荀子的重要地位。需要指出,提升荀子地位,必然會相對降低孟子的已有地位。孟荀之爭,是歷來較爲顯著的儒家鬥爭。雜文五編卷七有《黄朝槐荀子詩説箋序》一文,對爲自己的《荀子詩說》作箋者,提出了看法:
荀子説詩,固毛傳之先河。惟其學出於孟仲子,康成云是子思之弟子,則與“學於孟也”之孟仲子必非一人。似未可據此遂通孟、荀爲一家。雖然,孟荀之學,似異而實同,性善亦孟子蚤年之説耳。觀《盡心下篇》“口之於味”一章,前五者不謂之性,謂之命。後五者不謂之命,謂之性。則即荀子“聖人化性”之説矣。荀子齗齗與孟子辨,殆未見及此。余因此箋中有欲爲孟荀作調人者,故以斯言助之,似不必合前後兩孟仲子爲一人,然後見其異條同林也。
讀此不禁令人莞爾。俞樾表面上是在幫作者“調和”孟荀,但實質上是在說孟子自己放棄了性善說,而採取了荀子主張的“聖人化性”之説。爲何要化性?當然是因爲性本惡。不僅沒有絲毫爲孟荀作調人的意思,反而是直接揭孟子的短。俞樾曾直截了當地宣佈:“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賓萌集·說篇·性說上》)
按子思所作的《中庸》“率性之謂道”,“率”字之訓詁向有爭議。或訓爲循,或訓爲修。自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成爲科舉指定書,孟子之性善、率性之說盛行數百年。總之,孟子主張性善,故而率性即謂之道,因其性本善。荀子不然,以爲性惡,則須化性。孟子、荀子之分歧如此,影響的實際上是政治文化的每一個層面。法先王還是法後王,也是其中一環。
雜文四編卷七《〈皇朝經世文續集〉序》:
愚嘗謂孟子之書言法先王,荀子之書言法後王,二者不可偏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以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此法其法也。馬貴與著《文獻通考》,其自序即引荀子語以發端。然則士生今日,不能博觀當世之務,而徒執往古之成説,洵如《吕氏春秋》所譏病變而藥不變矣。
此處所言,也類似上文,雖說是“二者不可偏廢”,終究是贊成荀子所謂的“燦然者”,也就是法後王。
俞樾又作《荀子平議》,是其《諸子平議》中最爲用心用力的部分。王先謙作《荀子集解》,即將俞樾平議全部納入,且皆認可,足見其精湛審慎。俞樾爲《荀子》作平議,實際上可能是按《羣經平議》的標準在做的。他尊荀抑孟,既然宋人將《孟子》升格爲經,那麼《荀子》沒道理不可升經。俞樾就曾主張升《荀子》爲經(《賓萌集·議篇》)。升《荀》而不黜《孟》,而是主張二書同附《論語》之後,二人同列孔子左右受祀。故俞樾抑孟而不黜孟,因其知道孟子對於儒學傳承的巨大意義,與其“守本”的巨大價值。
法先王的“守本”與法後王的“求變”在俞樾的雜文之中都有所體現,當然求變以應世變的內容更多一點。但我們不能忘記,俞樾所處的是中西交涉的時代,他再怎麼求變、經世致用,對於大的時代來說,仍舊是像孟子更多一點。雜文六編卷七《詁經精舍八集序》:
嗟乎!此三年中時局一變,風會大開,人人争言西學矣。而余與精舍諸生猶硜硜焉抱遺經而究終始,此叔孫通所謂“鄙儒不知時變”者也。雖然,當今之世雖使孟子復生無他説焉,爲當世計,不過曰:“盍亦反其本矣。”爲吾黨計,不過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戰國時有孟子,又有荀子。孟子法先王而荀子法後王。無荀子不能開三代以後之風氣,無孟子而先王之道幾乎熄矣。今將爲荀氏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將爲孟氏之徒歟?則此區區者雖不足以言道,要是三代上之禮樂文章,七十子後漢唐學者之緒言,而本朝二百數十年來諸老先生所孜孜講求者也。
此處俞樾對於孜孜講求一生的禮樂文章,有其清醒的認識;對當時的時勢,也有其清醒的認識。時代在走向大變革,一如數千年前的大轉捩時代那樣。要學荀子,就應去學西學,此爲法後王,求變求存。要學孟子,那就是“守本”,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二者都是有價值的,雖然荀子要比孟子更積極,但孟子的價值並未因此而稍低。同時代的學者,以及後世的學者,對時勢和歷史皆少有這麼清晰的認知。
三、致世用而寫性靈:俞樾雜文之功能
“原本道德,根柢六經”也好,“有體有用,綜貫百家”也罷,取法之高,不等於所得亦高。俞樾之聲名在於經學研究,詩歌也還有名,但其文名實際上甚爲“不稱其學”,須知這是他的弟子章太炎的評價。雖然《清史稿》的評價是“不拘宗派,淵然有經籍之光”,雖然曾國藩極其讚賞他的文章,但更多人是說“其文卑弱”,且不顧此爲其雜文《序目》的自謙之辭。百年之下,唯有一周作人是其知己,從後世的角度,道出了俞樾之雜文的好[2]。周作人說:
平常講詞章的人批評曲園先生的詩文總說是平庸,本來曲園詩自說出於樂天放翁,文也自認文體卑弱,似乎一般的批評也還不錯。但是,詩我不大懂今且慢談,文的好壞說起來頗有問題,因爲論文的標準便有好些差異。(《學文月刊》一九四〇年第二期)
周作人認爲俞樾雜文中的序文尤其好看,在近代文章中極少有。他認爲文章有講義理的,衛道辟邪,不是好文字;講音律者,吟詠鏗鏘,聽之陶然;此外有講說話的,即將文章當作紙上的談話來看。這是白話文運動的遺風,極有見識。他認爲俞樾雜文就是這一類代表。在他看來,同樣是爲人作序,俞樾的序文有意味,有意見,有誠意,且還風趣。這樣的文章怎麼不是好文章?
然而文學史上的判斷,自然有其道理。俞樾的文章被低視,正是因爲他“不拘宗派”,又好寫,有求必應。首先說第一點。他雖然主張“原本道德,根柢六經”、“有體有用,綜貫百家”,又尊荀抑孟,但高頭講章是不會納入雜文的,自有其《群經平議》在。而俞樾又以集部本與子部相通(“今之集即古之子”),其作文皆含著子書之意。是故《賓萌集》有雜篇,就類似先秦子書內篇、外篇、雜篇之例。其後作文,索性就名之爲“雜文”。雜文不是時文,不是古文,而只是雜撰、雜纂(他有《曲園雜纂》),文無定法,不拘宗派。然而不拘宗派則各宗派引以爲仇讎,尤其是桐城派。
俞樾治經學雖然主漢學,但也不過分貶低宋學,只是痛恨“空談心性”,而崇尚訓詁。訓詁的歸止在於義理,這是他所強調的。清朝大儒多尚古文經,俞樾則主張公羊,尚今文經。可見他是真的“不拘宗派”。從他的《古書疑義舉例》可知,他擇善而從,學問很具有科學精神。回到作文這件事情,他就曾表達過對桐城派一統天下的不滿:“近世以來,論文者率以桐城爲文家正軌。夫桐城一派誠謹嚴爲法,然必執是以繩天下之文,則非通論也。”於是他寫雜文,不寫古文。在古文家來看,自然認爲他的文章不能入眼了。
什麼是雜文?以後觀前,周作人的說法雖不規範,但十分入神:
前幾年翻閱《春在堂集》,不意發見了雜文前後共有七編,合計四十三卷。裏邊固然有不少的好文章,我讀了至今佩服。但各樣體制均有,大體與一般文集無异,而獨自稱曰《春在堂雜文》,這是什麽緣故呢?我想曲園先生本是經師,不屑以文人自命,而又自具文藝的趣味,不甘爲義法理學所束縛,於是只有我自寫我文,不與古文爭地位,自序云體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雖半是謙詞,亦具有自信。蓋知雜文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也。照這樣說來,雜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於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統,總以合於情理爲准。我在上文說過,文體思想很夾雜的是雜文,現在看來這解說大概也還是對的。(《雜文的路》)
知堂先生說得十分透徹,“不與古文爭地位”而又“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外此不必多言。他盛讚俞樾文章的有意味,我想真正讀過的人都有同感。這就是俞樾高明的體現。須知他這麼多雜文,其實很多都是應酬文字。他都不推辭。《序目》中說得很坦白:“余所作不爲不多矣。……又性好徇人之求,苟有子孫羅列其祖父事實以告,輒曰是仁人孝子求顯其親者也,義不忍割。……然當代名公鉅卿之行事,所謂磊落軒天地者,亦多見於吾文,豈以吾文之鄙陋,而遂土苴視之哉?”他給自己找的借口是,雖然寫了不少孝子求顯其親的文章,但也有很多名公鉅卿之行事由其文而得顯留於世。這顯然沒有解釋爲何那些爲孝子所寫的文章要留到集中。其實不外乎他自己所說的“不忍竟棄”。因爲這些文章都很有意味。
如雜文卷二《李太夫人七十壽序》二篇,分別爲自作及替江蘇府縣作,甚可見其文章之妙。壽序之作無非褒揚,而容易流於陳言。而俞樾壽序,可說非常有內容,並無太多虛辭。給李太夫人祝壽,寫的却是李鴻章等人的豐功偉績,而歸之於母教。此節則二篇序文所共。俞樾自作的一篇,則將李夫人與唐朝李光弼之母相比,筆法縱橫,意象深遠。於祝嘏之辭中,可見晚清風雨飄搖之局勢,與李唐當年相當;而李鴻章兄弟,社稷之功又與李光弼兄弟相當。讀此祝壽文,可見晚清史,是其爲文務實之證。二篇同題却文體不相同,所述事實無異而筆法迥异,又足可見其文筆之老道,變化之多端。
俞樾不光與李鴻章甚有淵源,與另一名臣曾國藩也有所交游。集中卷二有《曾滌生相侯六十壽序》,以古之四賢來比較曾國藩,爲其功績作褒揚之辭。列舉史事、當時,以爲曾國藩之武勇過於諸葛亮,謀略過於陸贄,而其爲宰相過於范仲淹、司馬光。雖善頌善禱,讀後却令人不得不信服,是其長於爲文,而善於比較之故。而晚清時人對於曾國藩的評價,亦可從中見之。同樣亦有爲人作的二篇,一替丁日昌作,一替李瀚章作,依親近程度而爲辭,甚得其宜。
晚清重臣,若以曾國藩爲首,繼之而起者則爲李鴻章。雖前已有爲李太夫人所作壽序,而俞樾也撰有《李少荃伯相五十壽序》二篇。在其自作文中,俞樾否認當時人所常用的以李光弼比擬李鴻章,以爲李光弼不足以比,而轉以唐代李晟方李鴻章,明顯是因爲之前用古之四賢比擬曾國藩而因以推轉。其文一古一今,專用史事爲比,令人信服。
在衆多達官貴人的祝壽文字中間,也有一些真情流露的佳作。《汪蓮府兵部六十壽序》就是這樣的一篇文字。俞樾在此文中回顧了他十五六歲時初學舉子業,與汪相得甚歡,而後“彼此年少氣盛,以文酒相娛樂。跳踉大叫,放飯流歠。童僕匿笑,鄰里驚詫,不之顧也”。此情之真切,讀之令人莞爾,復生感觸。這樣的文字,多有意味,多麼真誠,何忍棄之呢?
俞樾所居,曰春在堂,曰曲園。其文集以春在堂而名,其人以曲園而號。俞樾“故里無家,僑居吳下”,而對安身之所情以寄之。他的園林記述之文,也極有意蘊,反映了傳統士大夫在經世致用之外的立身旨趣。《春在堂雜文》續編卷一有一系列文章,記述他的友朋和他自己的園林居所。從香雪草堂到琴心室,從曲園到留園、怡園,所作皆爲佳構,甚可玩味。蘇州園林向爲文史研究者所重,則不可不讀俞曲園之諸文。
我們從俞樾所記的名公鉅卿之行事,可窺見政治史的一些另外面向;而從他所記的小人物,以及友朋的園林,則更多可體知個體生命的升沉、時代潮流的印記,具有更難得的社會史意義。至於周作人所言,俞樾以一代經師論文體,走向公安派竟陵派[3],說金石文字之可證史,且與新文學相通,則仍待進一步研究。他的雜文中的一些見解,對於現代中國學術,尤其是“二重證據法”等的誕生,或許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
四、整理說明
本次整理,以南京博物院藏光緒末增訂重刊《春在堂全書》本爲底本,吸收蔡啟盛《〈春在堂全書〉校勘記》成果,也參考了相關研究成果;保留原有缺字符號□;古字不改,異體字改爲規範字;以他校、理校糾正一些錯字,出校;因避諱而改字或缺筆的“玄”“弘”“寧”等回改,不出校。
整理者分工如下:胡文波點校《春在堂雜文》《春在堂雜文續編》《春在堂雜文三編》並撰寫《前言》;王倩倩點校《春在堂雜文四編》前三卷,劉珈珈點校後五卷;張曉青點校《春在堂雜文五編》;白朝暉點校《春在堂雜文六編》;謝超凡點校《春在堂雜文六編補遺》,白朝暉參與點校《春在堂雜文六編補遺》初稿;汪少華審訂前四編與補遺,王華寶審訂第五、六編。
俞樾學殖深厚,用字用典俱甚古雅。整理者學識或有不足,點校有失誤不當處,尚祈方家指正。
胡文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俞樾全集》總目録
《群經平議》(二册) 王其和 整理
《諸子平議》(二册) 王華寶 整理
《弟一樓叢書》(一册) 王華寶、喬秋穎、傅傑、王博、張曉青、金钰 整理
《曲園雜纂》(二册) 顧莉丹 整理
《俞樓雜纂》(二册) 倪永明 整理
《賓萌集 賓萌外集》(一册) 滕振國 整理
《春在堂詩編 曲園自述詩 補自述詩 春在堂詞録》(二册) 謝超凡 整理
《春在堂隨筆 九九銷夏録(一册) 王華寶 整理
《經課續編 四書文 曲園四書文 曲園課孫草 經義塾鈔》(一册) 汪少華、劉珈珈、孫煒、王欣 整理
《茶香室叢鈔》(四册) 汪少華、顏春峰 整理
《茶香室經説》(一册) 魏慶彬 整理
《春在堂雜著》(一册) 孫幼莉、劉珈珈、黄曙輝、喬玉鈺、張龍飛 整理
《春在堂尺牘》(三册) 張燕嬰 整理
《春在堂日記 曲園日記》(一册) 孫煒 整理
《楹聯録存》(一册) 劉珈珈 整理
《右台仙館筆記 附耳郵》(一册) 王華寶、余力 整理
《薈蕞編》(一册) 謝超凡 整理
《七俠五義》(二册) 田松青 整理
《春在堂雜文》(三册) 胡文波、白朝暉、張曉青、謝超凡、劉珈珈、王倩倩 整理
[1] 參魏永生《俞樾“尊荀”析論》,《東方論壇》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2] 參黃偉《俞樾古文理論的承祧與新變》,《江海學刊》二〇一六年第六期。
[3] 參謝超凡《“傳統”的開拓,“現代”的先聲——俞樾雜文思想簡論》,《文藝理論研究》二〇一〇年第三期。
Copyright 2008-2018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35774号 地址: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200433
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總訪問量:2761263